可仲裁性涉及一种争议类型是否可以通过仲裁解决. 实际上, 可仲裁性回答了索赔主题是否保留给国内法院的问题, 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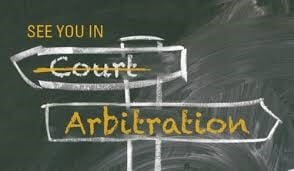 如果争议不可解决, 仲裁庭在其管辖范围内受限制,并且该主张必须改为提交国内法院.
如果争议不可解决, 仲裁庭在其管辖范围内受限制,并且该主张必须改为提交国内法院.
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的能力可能受到限制, 这意味着某些实体, (例如., 州或州实体) 基于政策考虑, 可能不允许订立仲裁协议或可能需要特别授权才能订立仲裁协议 (“主观可仲裁性”), 或基于主题的限制 (“客观可仲裁性”). 某些争议可能涉及敏感的公共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仅由国内法留给国内法院管辖.
争端的可仲裁性可能因一个国家而异, 首先, 由于不同的政策考虑, 其次, 取决于国家对仲裁的开放程度. 国家法律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更广泛的方向发展,允许将传统上超出其范围的事项提交仲裁。, 通常涉及刑法案件, 家庭事务, 或涉及专利的商业性质争议,[1] 反托拉斯法和竞争法,[2] 受贿, 腐败与欺诈. 这些问题可能仅限于政党自治, 作为国家或国际公共政策事项的体现.
关于可仲裁性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哪个法律支配可仲裁性的决定. 有关争端可仲裁性的法律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它是否由仲裁庭决定, 它将根据以下原则决定自己 胜任力; 由当事方之一同时向其提交争议的州法院; 在预留程序中; 或在执行程序中.
法庭在考虑哪个法律管辖争端的可仲裁性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仲裁协议法; 座位法则; 适用于争议的法律; 当事人之一的法律; 和执行地点的法律. 这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 芬坎蒂尼 案件, 在意大利法院和瑞士联邦法院发现相反的结果。[3]
争议的不可仲裁性导致仲裁协议无效. 结果是, 法庭将缺乏管辖权,裁决可能不会得到承认和执行.
可仲裁性的概念可以在第二条中找到, 段 1, 的 的 1958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纽约公约), 该条规定,每个缔约国应以书面形式承认一项协定,“关于能够通过仲裁解决的主题。” 此外, 也可以在文章中找到 5, 段 (2)(一种), 该声明指出,如果寻求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的法院发现以下事实,则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 “有差异的主体不能根据该国法律通过仲裁解决.”因此, 《纽约公约》第二条和第五条规定了仲裁法,为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提供了依据。, 但对在裁决前阶段应由哪项法律管辖可仲裁性问题保持沉默。[4]
从而, 确保可执行性, 仲裁庭通常应具体参照仲裁地的法律确定仲裁性. 如果争议不可根据该法律中包含的相关规则进行仲裁, 该奖项将开放给在该国撤销的程序,也可能排除其在另一个国家的执行.
的 示范法 专门规定了一些解决可仲裁性问题的规定,但未指明哪些事项是可仲裁的. 文章 1, 段 5, 规定示范法不应影响该州的任何其他法律,据此,某些争端不得提交仲裁,或者仅根据其他规定可以提交仲裁. 此外, 文章 34, 段 2(b), 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撤销仲裁裁决:, 除其他外, 法院认为,争议的标的不能根据国家法律通过仲裁解决.
至于 国际解决投资争端中心公约 (“ICSID公约”), 没有提及可仲裁性的概念. 文章 25, 除其他事项外, 确定由ICSID仲裁的事项范围, 特别是根据段落 4, 当事人可以明确将某件事排除在法庭的管辖范围之外. 因此, ICSID公约中的可仲裁性问题是采用“管辖权而非可仲裁性。[5]
尽管针对能够通过仲裁解决并因此可仲裁的问题类型定义统一的规则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人们可能会同意,关于国家法律之间可仲裁性的更多国际共识将是可取的,并将增加法律确定性.
安娜·康斯坦丁诺, Aceris Law LLC
[1] 例如, 在欧盟, 直接影响注册知识产权的存在或有效性的争议是交存和注册成员国法院的专属管辖权,因此不被认为可仲裁 (欧盟法规编号. 44/2001, 的 22 十二月 2000, 文章 22(4)), 而瑞士和美国则采取更为自由的态度,几乎所有知识产权纠纷都是可以仲裁的.
[2] 反托拉斯和竞争立法, 考虑到它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可能仅限于仲裁而不能仲裁.
[3] 热那亚上诉法院裁定,意大利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因为根据适用的意大利和欧洲禁运法规,该争端不可仲裁 – 看到, Fincantieri-Cantieri Navali Italiani SpA诉伊拉克 (1994) 撕裂. 戴尔’arb 4 (1994) (热那亚上诉法院/热那亚上诉法院, 意大利). 在平行程序中, 瑞士联邦法院认为, 通常, 根据瑞士法律,争议可仲裁的唯一条件是与财产有关的争议, 结束制裁并没有损害与瑞士所在地争端的可仲裁性- 看到, Fincantieri Cantieri Navali Italiani SpA和OTO Melara Spa v ATF (25 十一月 1991) 国际刑事法院奖 6719 (临时奖) 国际法杂志 (1994) 1074.
[4] Ĵ. DM. 卢等。, 比较国际商事仲裁, 克鲁维尔国际法 (2003), p. 189.
[5] Ĵ. Billiet等。, 国际投资仲裁, 实用手册 (2016), 196.